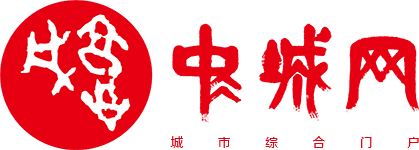出版家沈昌文睡梦中仙逝 享年90岁
中城网2021-01-10 13:03:15
据上观消息,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今天(2020年1月10日)清晨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其间,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出版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他主持下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佐良的“读诗随笔”,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多个兼具文学性、思想性的专栏,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1996年1月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等。
上海作家简平说:“沈公是我敬仰的长辈。这些年,他每年都带着新著来上海参加上海书展。沈公是我认识的老人中活得最有质量,最有智慧,最有趣味的人,和他在一起,会充满活力、豁达和快乐。”
沈公年事已高,这些年不再轻易出京,若外出只去两地:一是去美国看女儿,再一是去上海看书展。在2019年上海书展前赶出的《八八沈公》中,为庆祝沈公八十八岁寿辰,他的旧识、好友、徒子徒孙奔走相告,收集了三十四篇关于沈公的趣事文章。在这些出版人、学者、媒体人的文字中,一个天真、狡猾、机智、幽默、随心所欲、放浪形骸的沈公形象跃然纸上。
那年上海书展,《八八沈公》在友谊会堂举办签售会,沈昌文向台下读者问好,第一句话便是“各位叔叔阿姨们——”然后道:“我出生于1931年9月26日,没想到还有机会来上海温习自己的生平,回忆自己在上海受到的教育。”

2019年8月,《八八沈公》在上海书展举办签售会。沈昌文点评这本书的细节处处用心,比如封面照片,是特意安排他到专业摄影棚化妆好了拍的,“我自己看了觉得,怎么这么年轻美貌呢?”
顶让他满意的安排就是书一出炉,就能再来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我的初心在上海。我是上海人,就是上海的‘小赤佬’。在上海待了19年,这期间不只是得到了人的成长、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有了指引。”沈昌文说,当年曾在上海接受电报接收培训,差一点儿成了特务,是一位共产党员告诉他,要认清形势,还让他去学俄语。“霞飞路上有一家餐厅的罗宋汤好吃,我以前只知道去喝汤,后来就找那里的厨师学俄语。不仅学了语言,他还告诉我很多苏联的新思想。”
到北京后,沈昌文慢慢从校对员做到了主编,他说,“之所以在北京做出了些事,就是因为在上海得到了党的教育后认识了自己的前途。”他回忆自己曾得到出版界前辈的庇护,后来在他的身后,又有一串新的出版人跟随着。“我知道出这本《八八沈公》背后的意思就是要我不忘初心。”
“沈公的初心就是怎样真正做好出版发行,拿出读者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书,同时让作者在他的诱导启发催逼下产生最好的成果。”学者葛剑雄说,沈公的饭没有一顿是白吃的,他所抓住的出版线索都在不经意间露出端倪。“沈公做的事远远超出一般出版人、出版商,而他又确实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学者江晓原记得,自己曾给《读书》杂志写过一封信,希望杂志能起个正式的英文名,“这个建议三联至今没有采纳,但在沈公家里,我却意外见到了自己那封‘读者来信’。它竟到了沈公手里,还被一直留着,甚至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一封信。”
“沈公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化商人应该如何走,应该如何做出版、做文化、面对读者。他永远是我们的师父。”出版人俞晓群说,后辈们与沈昌文的相处十分单纯,就是精神上的追随,心灵上的认同。
在《八八沈公》的编者介绍里有这样一段——他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他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是“安徽打工妹”心中永远的偶像。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和“复印机小姐”谈恋爱,随身携带着装有五十页“著译者”和“关系户”的PDA。当然,也少不了他对书的“痴爱”,他自成一派的“出版经”和处世之道。他是智者,他是仁者,他是狂狷者。他是常背着双肩包,自称“不良老年”,独一无二的沈公。
那场签售会最后,沈昌文透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八卦”:“我到北京后因为不适应天气生了一场大病,回到上海养病时去大沽路找蒋维乔先生学了气功。这气功的要诀就是静坐。在北京我经常坐上公交车一晃就是几个小时。别人看不懂这老头干什么,其实,我是用北京公交车上消磨的时光,纪念着上海的马路。”
“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来上海了,看到上海的景象,上海的朋友,我很感动……”言犹在耳,沈公远行。

沈昌文:我不是知识分子 我是知道分子
中国经济网 2004年12月20日
“万人迷”和“便衣神仙”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沈昌文年过七旬,精力还是无限,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骑一破旧“永久”,穿梭大街小巷,出入酒吧饭局,整日帮闲,贩卖资源,口说broken English,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人谓“不良老年”,不亦乐乎!
看着他笑得阳光灿烂,一览无余,你不由得会想:这就是《读书》曾经十年的主编,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吗?这就是出版界的灵魂般的人物,读书界旗帜性的人物吗?这就是那个“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的可敬的思想作俑者吗?这分明是一个超级卡通,超级好玩的老顽童的形象呢!我纳闷导演为什么不去找他做喜剧明星呢?可是说他是老头又是不准确的,他的想法活跃,思路迅捷,根本不亚于年轻人呢。
他坐在你面前,为人隐忍周全,言辞放肆坦荡,态度质朴谦逊。他一生在紧张和颠沛中度过,从事的是最严肃的思想的传播事业,但是他在工作之余,说,听听邓丽君吧,吃吃北京最好的饭馆吧,泡泡最好的咖啡馆吧。年轻的,年老的,都是朋友,他没有隔阂,全无避讳。
“三联”编辑部的年轻编辑,私下里给他一个雅号:万人迷。还告密说,赫赫,沈公的女朋友可多了!他不但迷倒了十七岁到七十岁的女性,就连男人都很迷他呢。这说的是沈公的性格和接人待物的态度。
忽然想:这天上的神仙,要是穿了便装来到世间,也就是沈公这副笑嘻嘻、宠辱不惊的样子吧。
上海小学徒
这是一个好玩的人,而他经历的,是一个并不好玩的时代。
1931年,沈昌文出生于宁波。父亲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沉湎于鸦片,家产败光,债台高筑。他去世的时候,祖母母亲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母亲抱着3岁的沈昌文连夜出逃,从此在上海飘摇不定。
13岁,他进入上海的首饰作坊“银楼”当学徒。
学徒要抱孩子、买菜、做饭、做手艺活。“我当时抱着老板3岁的女儿,后来我走的时候19岁,她9岁,老板就要把她许给我——那时宁波人很讲究这个,把特别年轻的女孩子许给人家。后来这位小姐一直在上海,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去上海,经常和朋友一起去看她。”
他还常常侍候人们打牌,来往的人特别多,有国民党人,有土豪劣绅,也有地下共产党员。他就在这样伺候人的生活中,懂得人生的三昧。
他到底是天生乖巧知趣,深得老板和顾客们的欢心。而他生性爱读书,用给一个工厂老板做假账赚来的钱做了学费,抽着空儿,前后念了十几个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世界语、无线电等,最后一个学校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他的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摄影记者,自诩自己给影楼的MODEL拍照,而他们的用光又是如何如何地讲究。他还学过无线电的“报务”,“就是‘嘀嘀嗒嗒’的那个东西”,他的发报速度达到每分钟100~120个code。
1951年初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考校对员。沈昌文便来到了北京。他懂得一些俄语,翻译了一些苏联出版专业的书,领导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不但被留下来,而且在1954年,从一名校对提拔为社长秘书。“我的命运就全部改变了。”
1954-1956年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候。1957年“反右”开始了,开放就终止了。
上世纪60年代反对赫鲁晓夫,因为组织安排,沈昌文负责研究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修正主义”,可以去很多地方包括安全部查资料,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我喜欢看外国书,崇洋媚外,喜欢做翻译书的编辑。”
60年代要“反资反修”,很多文革时期长大的人,都偷偷看这些“资”、“修”的书。因为政治上很受信任,沈昌文被调到一个叫“中央宣传办公室”的地方,他们就翻译很多这样的“灰皮书”如《新阶级》,“黄皮书”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做了许多这样的书给领导看,直到“文革”期间被下放。
《读书》10年
1979年4月,《读书》创刊。聚集了当时一代一流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才学和能量。“读书无禁区”,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从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读书》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上的营养。”雷颐说。《读书》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引领,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是1980年三四月份过去的,那时候《读书》已经创刊好几期。刚去的时候,主编是陈原,副主编史枚。两个实际主事的都是非党员,组织上要派一个党员过来,做三联书店编辑部的主任,就是我,而我又是这两个非党员的徒弟,所以我心里有数。
“我对两位老人家很尊敬,弟子之礼甚恭。史枚是一个十分耿直的知识分子,而我可以‘稳住’他,也可以调节内部人员的矛盾,这就是‘和稀泥’。后来史枚去世,1981年我担任了《读书》的副主编,实际上就是当家了。”
陈原告诉沈昌文:以文会友。“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
沈昌文后来才有所领悟:“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
1986年主事《读书》后,他的方针是:“自由主义的,左的,我都发表。”他要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世界太复杂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满。
“我非常欣赏现在一个词,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我倒是都知道,可我不是知识分子。”
他不主张只把《读书》变成一个学术刊物,主张用“外行”来做编辑,不大赞成请学者来编《读书》,因为后者一定会有倾向问题。
在阅读上,他强调“可读性”。“但如果遇到很有观点,但是不可读的文章怎么办呢?我在编辑部立了个规矩,这样的文章一期不能超过一篇。”
“我们《读书》的经验是:讲穿了,想表达一种读者最想听的话,如果想听的话不让讲,就想各种曲折的办法表达民意。去查资料去。找渊源,跟有学问的人去讨教。”
外圆内方
“宽容”,沈公屡次提到这个词。他理应有着切肤之痛。过去历次运动,无事三尺浪的年代,他是出版社里负责向上头做检查的人。他多次表示自己十分幸运,或者是,精于检查之道,以至于每次都有惊无险,顺利通过。说到这里沈公总是要笑,眼睛都眯起来了,好比一个得了糖果吃的小孩一样得意非凡,而里面五味俱全,有庆幸,有快乐,有酸楚,有自嘲。
“做编辑工作当然要有自己的眼光,但是更要有‘手段’。对社会上的不公正,如果不能直接批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各种曲折的手段,用马克思的语言去批评现在的现实。这可能是我可取之处,也是我的不可取之处。”
黄集伟曾经评论沈昌文的《阁楼人语》(沈公主编读书十年的编辑手记):他恁多“抱怨”或“表扬”竟一一演变为一个思想经营者的“市场”策略: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沈公的“雅痞风致”与“慧眼仁心”其实互为表里,相互牵动。
他的门径似乎是“外圆内方”。过去中国出版界、思想界斗争之复杂和尖锐,我们今日恐怕还是不能想象。沈公生性豁达乐观,恐怕也有难言之隐,无法陈述。他说话带着诙谐,自有他的放肆,也有他的知趣,雅痞之风,但是大概是话中还有话,只怕是有心的人,才可以彻底明白。
“幸福不过是你的想象”
如果有人心中不忍,说沈公你应该颐养天年了。但这样的话,对他说更是不忍。他哪里舍得休息?他热衷于“小道消息”,热衷充当“思想小贩”。在这里头他有多少乐趣,多少好玩的东东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你又如何舍得让他放弃自己的乐趣呢?
人物周刊:你整天都笑呵呵的,很高兴的样子,有什么秘诀吗?
沈昌文:我练一种名叫“小周天”的气功,师傅是蒋竹庄。他是大知识分子,当时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他练的气功以哲学为基础,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静止”。因为这个,大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还用笔名“二十八画生”写文章批判过他。50年代我去上海,他给我面授机宜:人要破除我执。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要想不开’。就是不能执着于一件事情。你把它想开了,想开了不就高兴了吗?
人物周刊: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沈昌文:幸福不过是你的想象。你认为这是不幸,你认为这是“幸”不就行了吗?人生有限,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走自己的路,能做到了,就是幸福。这符合我们宁波人的俗语:除死无大事,讨饭永不穷。所以活着就是幸福,我的想法便是如此。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有什么缺点?
沈昌文:我的缺点是不能够专业做学问——思想太活跃。经常心潮澎湃,不能长久地呆在一个屋子里。再一个是胆子小,只守着一个专业,只守着一个老婆。
网友评论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