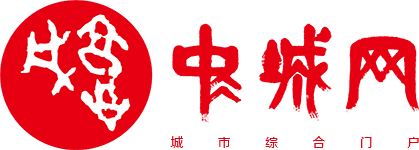刘福垣:中国城市体系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
中城网2008-03-01 21:08:05
中国城市体系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
刘福垣研究员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内容提要
刘福垣研究员认为:
1、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已经面临崩溃,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外需为主转为内需为主;
2、中国城市体系发展要“以中为重”,重点发展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
3、现在所议论的废除市管县的想法,又将犯一个战略性错误,要造成一次更大规模的混战;
4、房地产热了就压房地产的价格,这路子根本就不对,住宅现在是严重短缺,真正给产业工人(农民工)盖的房子还没有动工呢。
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确定我们的城市的空间结构?这种结构的调整如何促进或服务于我们国家发展的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因为你建立什么样的城市体系,它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是紧密相关的。我想起了这个题目,也正是我们建设部刚刚做完了一个中国城市体系的规划,要我去论证,我就发现有必要讲一讲这个问题。
中国当前的经济处在一个什么阶段?现在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习惯于从类型看问题,盯着GDP,盯着物价,盯着进出口这些具体的指标,在冷了热了,高了低了上面做文章。一切战略性的问题,都存在着我们对国家,对城市当前的阶段没有准确的时空定位。比如说,我们的“十五规划”眼看着结束了,“十一五规划”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干着,我已经看了20多个省市的规划草案的文本。很遗憾地说,这些文本在对“十五”后评估的时候,都是轻轻地一语带过:“十五”超额完成了任务。这话也正确,从GDP的角度确实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尤其地方上有两位数的增长,当然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十五规划”的重点,它的主题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遗憾地说,当时提到的四个层次:产品层次,产业层次,居住层次和城乡层次。这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到今天为止,不仅没有好转,几乎是全面逆转。产品依然大量地积压,能源电力全面紧张,三大板块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四个层次的矛盾转化的任务没有完成。要害在哪?就是没有对战略性调整破题。为什么破不了题?就是因为我们只抓日常生活中的运行,没有对这个战略阶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简单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处在工业和农业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并存,而且是三七开的阶段。我们中国的经济版图,就相当于太级图的阴阳轮,一半阴,一半阳。城市的工商业已经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它跟欧美日的生产方式没有时代的差别,它在阳面,而阴面就是我们8亿多农村人口,2.6亿的农户耕种的18亿亩土地,现在平均每户总共不到半公顷。这些不能自给自足的小农户,他们的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五千年存在的小农经济在我们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活化石。这样两种生产方式不能用先进和落后来描述,它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它的再生产规律是不能对接的。既然是这样一种局面,按照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的原理,中国还姓农,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仅仅看到660多个城市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以为我们现在的水平很高了。但是我们的农村,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要给它定性的话,它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两种生产方式、二元社会结构并存的一个国家,按照这个阶段,它的真正的战略性调整调什么?是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人口的空间结构。说白了,就是减少农民。我们去年GDP可以说是“高”增长,但这个高要打引号,它相对于全世界发达国家GDP的水平看是高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现在转化二元结构的需要而言,它是不高的。所以不能紧盯9点几,或者是11、12 ,就说我们的经济热了,我们的经济速度并不高。我曾经在日本跟他们讲,我们的这个9.4是人均不到1500美金的9.4,你的1.8是人均3.8万美金的1.8,是没有可比性的。不能说我们的经济就热了,高了。热和高看什么?看就业。我们现在好多人把西方的一些模型拿来,一会上去,一会下来,以为这就是周期了。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中国没有经济周期,它只有政治周期。如果说有的时候热,是虚热,是政治热,不是经济热。看经济热不热,要看就业。而我们现在的就业和真正政府的失业率,我们说不清楚。城市登记时它根本不讲,不反映问题。有一个指标可以反证这个问题,那就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社会犯罪率的直线上升,它反证我们的失业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既然如此,我们现在的9点几的增长速度,对于中国来讲,不是高速度。如果我们结构性的矛盾,真正实现了战略性的调整,那么我们的速度应该比现在还要快一点,绝不是现在这种增长方式。去年的九点四,城市化率才有零点五几个百分点的增长。
增长速度在中国有两个数字,我们只认识了一个,就是GDP的增长速度,另外一个速度是生产方式转化的速度,它的标志就是城市化率,就是减少农民的速度 。如果我们到2020年,想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每年至少要减少两千八百个农民,也就是现在的4户农民,得有3户进入我们现在的城市。那么大家想想,它需要多少就业岗位?每年至少要两千多万。要满足这两千多万的就业,我们现在不转变增长方式,就凭现在这种拼土地、拼劳力、拼资源,不行。今年上半年,两个三角地区经济的下滑,带有它的必然性,不能埋怨是宏观调控造成的。宏观调控本身也就是一个百分点左右,搞得好上一个百分点,搞不好下一个百分点。真正经济内在的、潜在的力量,是我们的二元结构要减少农民给我们提出的任务。因为我们现在计划生育虽然很严厉,但是我们每年新增的农民,新增的农村人口差不多相当于以往澳大利亚的人口,也就是一千二三百万。每年如果我们把相当于这些数量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我们才是零发展,如果我们减少的速度不如它增长的速度,那我们是负发展。要绝对正发展,要想赶上发达国家,我们至少要以一点五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农民。以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的。我们单位土地面积的就业量,新的开发区、特区实际上还不如我们的建成区的人多。我们现在的开发区和特区,就把中国当成了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加拿大这样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一个企业大约占了相当于四个企业的地,所以现在两个三角的模式,它的边际效益已经是负数了,它在五年前就应该转变发展方式,晚了五年,所以现在受到了惩罚,不是宏观调控造成的。我可以说这两个三角,十年不给它耕地,它应该还有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为什么?因为它现在一个企业占了四个企业的地。我在宁波当过副市长,2003年上半年占的地就相当于一个省的建成区的3.8倍。现在的企业占地,百分之三十的绿化,花园式的农场,这样下去有多少地?每天一个百分点GDP,得拿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必须转变增长方式。按照这个二元结构三七开的阶段转变增长方式,我们现在做什么?从全国来讲,主要是要把投资拉动型的、单位拉动型的增长方式和投资模式转化为消费型和内需拉动型,这个转变是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不转变中国就翻车。我可以给大家作个比喻,我们整个中国,现在是相当于一个内脏,七经八脉都有病,都不通,行走靠什么?靠一个大拐杖。这么粗的大拐杖正在腋下拄着,支撑了体重的百分之七十。我们现在GDP的盘子是十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亿,其中进出口占了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拐杖是由外贸、外出、外企这三外拄着,如果这个拐杖一失掉,我们这个大巨人“砰”一下倒地,就是这样一个危险。所以,欧、美、日甚至墨西哥、巴西都看到了中国的软肋,知道我们的命门在这个拐杖上,所以跟我们搞贸易摩擦,逼着我们人民币升值。不解决这个拐杖问题,我们是没法再继续前进的。那么,有的人会说,日本是贸易帝国,人家的出口那么多。但是,你知道占GDP的多少?日本进出口加在一起,只占GDP的百分之十五。出口百分之十,进口百分之五。美国是百分之二十二,百分之七十八、百分之八十五都是靠内需。而我们现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实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是采取了像韩国那样的相反的战略,这是相当危险的,必须启动内需。那么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必须推翻三座大山,也就是社会保障、居民教育和居民住宅。现在社会保障不到位,是压在我们内需上的第一座大山,是最高的那座山。老百姓不敢消费,一个劲地攒钱,攒钱就是攒失业。很明显,上个月的存款八万二千,那么就是有八万二千的东西没有变现。我们居民储蓄率已经百分之三十七,国民储蓄率已经百分之四十三,那就是说,相当于生产这百分之三十七的产品的人就要失业。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攒钱就是攒失业。美国人现在储蓄率只有零点六,是负增长,不但不攒钱,还改成借钱消费。不转变发展观,不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不行了。我们要把义务教育做到位,把社会保障解决,把我们的普通民居解决。
我们现在对城市问题的判断,好多都是失误的。房地产热了就压房地产的价格,这路子根本就不对。住宅现在是严重短缺,真正给产业工人盖的房子还没有动工呢。什么是当代的产业工人?就是那些农民工。他们创造了我们GDP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他们的生产增加了,城市应该给他们六十平米的住宅,同时还要享受国民待遇。他们现在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劳动,月工资只给五六百块钱,我们的民工租不起房子。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住宅的租金比人们的工资还要高,这是绝对不正常的。毛病出在哪?出在土地批复。我们只有把土地批复变严,使房地产分级流通,降低房屋的价格,降低租金,适当地提高工资,使这两个对接到什么程度?对接到月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以内,可以租到六十平米的房子。那也就是说,至少我们民工的最低工资应该是一千元。两口之家,两千块钱三口人,他要拿出来六百块钱解决住,其中的房租也顶多占百分之二三十,还有水电,你不能让他收入的大部分都用在房子上。什么用未来的钱圆现在的梦,鼓动大家都买房子,这是资产阶级的政策,造成一个人人都是有产者的假象。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我们的广大工薪阶层就是个无产者,他就是两只手,就是要靠租房子解决问题。真正有钱的,买房子也不买这种公寓楼,他们去买那种别墅楼。因为这种公寓楼是假买,现在大家买了,不过是多交了几年房租。上边一家,下边一家,左边一家,右边一家,哪是你的?你不过就是租了一个空间而已。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这三大问题解决了,城镇化的门槛就降低了,农民工就可以享受国民待遇,从二等公民变成农民,这是从我们的体制模式改革。
从发展的模式上,我们的城市体系按照现在的结构不行。怎么调?我提出了“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当务之急就是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要加速扩容,要建立这样一个城市结构,不要急于继续向大城市锦上添花,也不要到小城镇去雪中送炭,要把我们经济上的人、财、物集中往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让它加速扩容。因为它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矛盾转化的关键点。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毛主席问耀邦同志:你说什么是政治?耀邦同志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主席说你说的不行。于是耀邦问主席:您说什么是?主席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在延安时代,如何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就是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重中之重、核心是什么?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的民主党派。要抓中间阶层,它和旧阵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新阵线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谁争取了中部,谁就获得了胜利。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在哪?我们这四个结构性的矛盾的中部在哪?我在书中曾经提出了五个,在这里先说这两“中”: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因为我们的660多个城市里边,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万以下的小城市,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还有三万到四万的小城镇。大家都知道,民工潮不往小城镇走,民工潮呼啸而过都到了大城市、特大城市。北京城500多万民工,为什么?因为只有大城市才有吸纳力,聚集了足够的人气和士气,才能使社会分工深化,才能创造就业岗位。那么我们现在的中等城市,大部分都是地级市,都是周围农村人口密度大,管着五六个、十来个县城的城市,它现在有三五十万,二三十万,有一定的聚集度,有一定的吸纳力,但是正在处于爬坡的阶段,吸纳力不够,常常是民工潮呼啸而过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把这样的城市做大,加紧做大。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我们的城市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中等城市。从原则上说,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宜足则足。但是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城市结构和重点,有城市工作的重点,我们应该放在这。放在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对我们的增长方式的转化起着重大的作用。中部的崛起就是中国的崛起,中部的崛起等于给我们中国的国内市场打通七经八脉,起到了一个针灸的作用。现在中国强调对外开放,但是不强调对内开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依靠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的扩容来落实中部崛起,使它吸纳周边的农村的劳动力,减缓民工潮对我们的交通和社会结构的冲击,这样我们的内需市场才能起来。我们现在的交通很紧张,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紧张的程度来设计我们的交通,我看要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我们的综合交通体系不配套,如果我们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都发展起来了,特别是这二十五年,那么我们的化农民为市民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性调整的问题,我们的内需启动的问题就解决了。
中部地区不能再照搬东部地区的模式,不能再拼土地,再拼劳力,再搞那种送礼性的出口。我们现在好多人都在讲提高国际竞争力,我看在我们国内,现在大家争的,提高的是送礼的能力。因为我们整个出口,东肺西肺,都送给了外国人,而我们的小老板们的收入在哪?就是在扣工人工资这一块。这样一种送礼性的出口,我们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去年我们就消费品这一项,送给美国人一千零五亿,相当于13亿中国人,送给每人是六百块钱。我们的东西给人家,拿回来一张带油墨的纸,钱也给人家,我们忙乎什么呢?中部崛起,中等城市扩容,它主要是以内需为主,而且按照以人为本,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升级,你要什么我就干什么。那么我认为那三座山就解决了。同时我们的增长方式也搞配套,这就需要大中小城市配套,以它的地级市为中心,把县城连起来,形成小城市圈,然后若干个地级市再形成中城市圈,然后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再搞大城市圈。我们就大圈套中圈,中圈套小圈,形成我们的区域结构,这样形成国内市场,七经八脉打通了。如果不这样从地区分工,从结构上解决问题,按照现在大圈小圈,大地区小地区,都把自己的行政辖区当作一个国家来管理,从封疆大吏到县太爷,把自己的行政辖区都当作大国来经营,包括这一次“十一五规划”我看了,还是没有根本改变,都以大国自居,一二三产业,根本不和周边的配套。所以不搞小城市圈,中城市圈,我们这个问题就很难弄了,永远是依靠外需。而现在要出问题了,要翻车了。如果我们真正解决了我们自己的中部城市崛起,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县级城市要成为重点,那么县级市也搞它个二三十万,三五十万,中国的城市化的问题就基本解决,我们从发展中国家就进入到发达国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跟日本一样,虽然出口很多,但是不是大拐杖拄在腋下,而是拿在手上,它是捞财的工具,看哪有利往回捞一下。我们现在的中国完全是倒着干。自古以来搞贸易商人很多都是物易相贵,我们现在是物易相贱,整个是反的。人家拿着拐杖捞钱,咱们拄在腋下。所以我们联合国的外交官不行使常任理事国否决权,不高兴了,用一个弃权票也就算了。我们的年轻人认为我们的外交官是骨头软,其实这不是骨头软,这是政治智慧。如果我们硬一下,长三角、特别是珠三角有几万人要下岗。所以我们要进行体制改革,以城市布局占领国际。这是我说的第二层意思。
最后一点,要想落实“以中为重”的发展观,要加速中等城市扩容,那么现在所议论的废除市管县的想法,我认为又将犯一个战略性错误,要造成一次更大规模的混战。因为现在这些年,省里都感到大权旁落,县级政府也感到跟市来一起拔河不太合算。这两家合起来,就想把市甩了,所以现在有些省里面看到哪个县搞得好一点,就来个计划单列,现在学者们也在议论市这一级是多余的,要把它拿掉。我认为,市管县存在问题,需要完善,但是绝不能动摇。在这个阶段,要中等城市扩容的时候,如果大唱县域经济,两三千的县级单位都跟上边捆在一起,最后我们是又一次的重复建设,又一次重构配置。所以我主张淡化县域经济的概念,强化市域经济的概念,特别是中圈、小圈、大圈。我们是要搞经济计划,不要再搞行政计划。中央政府给你的地盘是行政管辖的范围,不是经济区划。搞县域经济现在搞成了每个省都是小康省,每个市都是小康市,每个县都是小康县,每个村是小康村,每个户是小康户。现在咱们的指标体系就差村没有了,都在搞竞争指标体系,大家都在忙,反正县也在达标排百强县,市也在达标排竞争力城市。我告诉你,这是富人给穷人设的八卦阵,这是六十年发展中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秘诀。为什么?我们就是进了人家的八卦阵。什么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不知道化什么,不知道它的时代标志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光抓前面那个字,工业化抓工,城市化抓城,现代化就抓现,就达那个标,不知道现代化的时代标志是生产方式的转化,也就是剩余价值率,没有一个指标是现代化指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转变发展观,转变模式,要求改革城市体系,改革城市的工作重点。
2005年9月 9月13日,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
(中国城市网总编室姚敏根据录音整理,摄影:姚敏)
网友评论
暂无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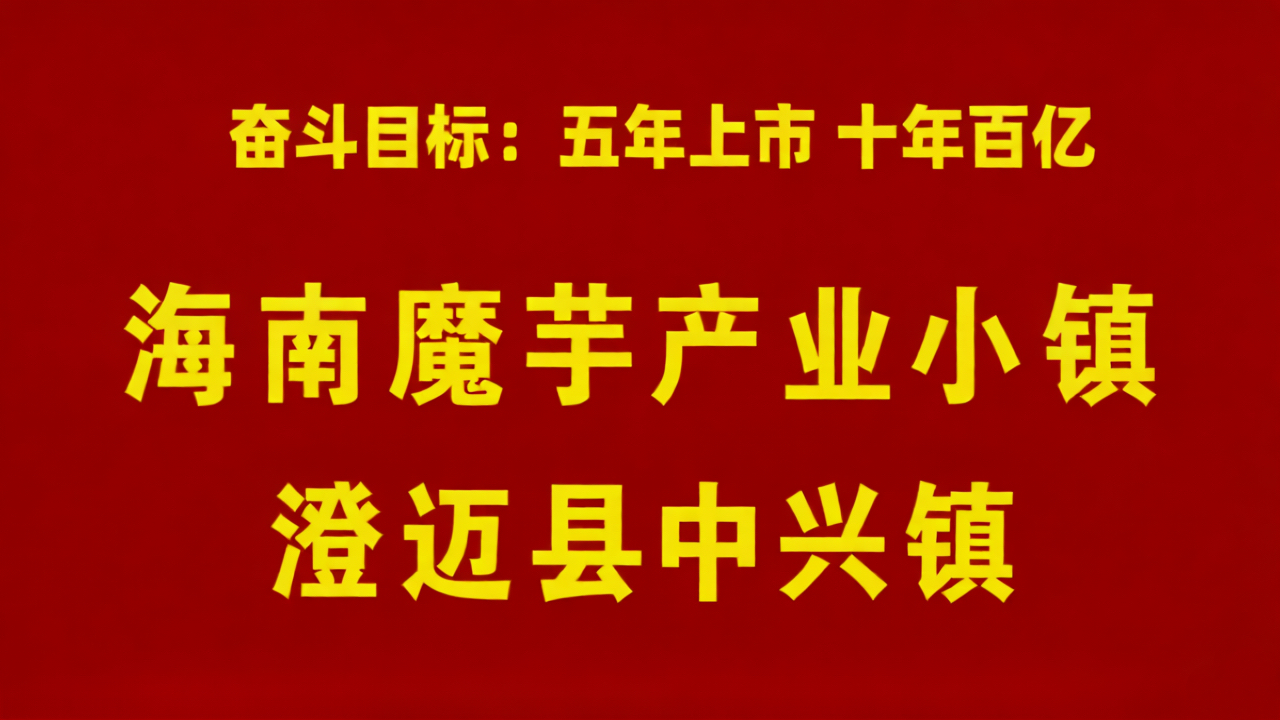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