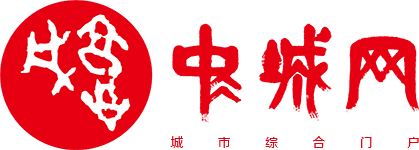房产:行政干预是暂时的,市场调节是永恒的
中城网2008-03-14 12:19:47
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它的健康发展可谓关乎民祉,系乎国运。无论是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是现代的“居者有其屋”,都不过是代表了人们的一种朴素的愿望。然而,近几年,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不规范操作,一些地方的房价大大超出了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房产新政后的中国楼市究竟向何处去?2005年9月,中国城市网总编室编辑姚敏就有关问题对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副总裁宋乃娴女士进行了专访。宋女士曾经历任设计院院长、规划局局长,之后又当了八年的市长,现在身处房地产市场的第一线,她对于当前房产形势的理解和看法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种更加多样化且深刻的认识。
中国房产:行政干预是暂时的 市场调节是永恒的
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副总裁 宋乃娴
行政的干预是暂时的,市场的调节才是永恒的
姚敏:近期,随着国务院调控房地产过热的两个“国八条”和七部委出台的楼市新政等政策相继出台,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次的宏观调控?
宋乃娴:国务院的宏观调控是从2003年6月份的121号文件开始的,整个房地产贷款的门槛都提高了。接下来的18号文件中很明确地提出了房地产是一个支柱产业,后来出台的国八条以及温家宝总理的新八条等等,实际上都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控,而把对房地产的调控作为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作为国家来说,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还是必要的。这些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比较乱。挖煤的、发电的、搞旅游的、开饭店的、做成衣的、卖家电的、做原子弹、发射导弹的都成了开发商。由于不懂房地产,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价值建出高品质的建筑,造成资源的浪费;或受利益的驱动,资金流向了盈利高的别墅、高档住宅,造成不同品种住房的比例失调;由于房地产业60%的资金来自银行,加大了金融风险。所以,国家从金融、税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这个市场,调节这个市场,我认为是适时的,是必要的。特别是“国八条”里把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放在了首位,清楚地说明要通过建经济适用房和普通住宅来解决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东南沿海和西部之间是不平衡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是不平衡的,北京、上海和一般的城市之间也是不平衡的。如果用同一个政策来规范全国的市场,这里边就会存在问题。好比患病吃药,有的地方得了这个病,下这个药来治,但是有的地方还没得病,如果也一视同仁,都来吃这药的话,就可能出现有的地方治好了,有的地方吃坏了的情况。所以,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行政的调节只能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市场的调节才应该是长久的,是最有效的。
政府有点“矫枉过正”
宋乃娴: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是有一定泡沫存在的。我记得前几年上海和南京就已经不搞经济适用房了。开发商受利益的驱动,建了大量的高档住宅和别墅。上海真正能买得起别墅和高档住宅的大都是外边的热钱,不是说这些人来买高档住宅和别墅不对,也不是说开发商开发这些房子不对,而是作为政府,应该考虑到广大的真正居住在上海的1000多万市民的利益,想办法解决普通市民的住房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从2003年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个人认为,文件中提到的不正当需求、严格控制别墅、高档住宅的土地供应都是有点矫枉过正了。真正从房地产的发展来讲,高档住宅有需求就是要盖,政府应该通过调整税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用来解决中低收入人的住房问题。而不是让高档住宅和别墅都别盖了,都不盖的话,怎么体现土地的价值?比如说在上海、北京的核心区,土地的价值就是高,只有盖高档住宅、高档写字楼、高档商业房,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才能得到符合价值规律的土地出让金和税收。政府的财力增加了,才有能力解决市民住房问题。这样,房地产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才能解决,社会才能更加稳定。
姚敏:您刚才提到目前国家的调控有点“矫枉过正”,为什么会这样呢?
宋乃娴:当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时,往往需要采取暂时的矫枉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由于大量的资金流向了别墅和高档住宅,经济适用房和普通住宅少了,所以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呼声非常高。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一直是没有开放的,大家都靠银行,而开发商把银行的钱拿去建别墅和高档住宅,这就不合适。所以现在国家通过控制金融贷款,把用来建别墅的土地和资金基本上控制住,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但是它不是永远的。在目前阶段,通过行政的手段把金融控制住,让它的资本流向更加平均一些,这是对的。但是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可能的。你要想让房地产健康发展,那就要照样盖高档住宅,只要你有钱,盖多高档都行,只要有人买,这是市场的调节。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建立相应的、完善的税收制度来进行约束,用收的钱来解决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
如果我们的金融、税收、土地等制度合理、完善、层次分明,政府就不用担心开发商都去搞高档住宅、别墅或都去搞普通住宅了。开发商会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对市场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产品。建高档住宅、别墅的利润高,但有可能资金占有量大,周期长,风险大,后期销售是未知数;而建普通住宅或经济适用住房,利润低,但资金压力小,风险小,后期销售有保证,可能开发商更愿意搞经济适用房和普通住宅。这就是市场调节,市场需求对开发商来说是最重要的。
另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现在非常快。大概到2020年,我们的城市化会达到60%左右,这就要增加大概2亿5到3亿的人口。增加的这些人就有住房的需求,这还没包括流动人口。所以,中国的需求不是一年两年,北京也不是说奥运会完了就到低谷了。因为我们居民的住房问题还没有达到标准。我们现在的住房面积大概是人均23平米,台湾是28,新加坡是30,美国达到了60。所以说我们的需求还大着呢。我记得有家机构对中国人的住房需求做过一个测试,大概80%的人对自己现在的住房不满意。再加上中国人有买房子置地的传统,因此,住一室一厅的想变成两室一厅,两室一厅的要变成三室两厅,所以这个需求是不断的。因此我觉得还是要由市场来决定房地产的发展。
提高信贷门槛是必要的
宋乃娴:总的来说,现在开发商一个项目下来,大概60%用的是银行的贷款,包括前期投入的大量的贷款,还有个人抵押贷款。这样一来,银行的风险确实比较大。把金融风险控制住,我觉得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个人的抵押贷款来说,我觉得只要把范围、标准定好,应当放松、降低门槛使无房户买得起房。中国人借钱还钱的意识是比较好的。作为银行来讲,个人抵押贷款的不良率实际上是最低的(0.12%),所以我认为,个人的抵押贷款其实可以放松一些,至于开发商作为项目上的贷款,是应该有所控制的。
姚敏:也就是说要抬高信贷的门槛?
宋乃娴:我觉得一定的抬高还是有必要的。否则有的开发商他一点自有资金都没有,几百万也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然后就去圈钱,圈钱自己又没有能力。另外,还有很多根本不是搞房地产的也进来了,他自己又不会运作,这样就会增加金融的风险。
调控要避免一刀切
姚敏:房产新政实施一段时期以来,相对以往热闹的房地产市场,无论是成交量还是销售额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有人就说房地产的冬天来了,甚至还有开发商提出了“救市”的主张,对此,您如何看?是真有其事还是开发商在夸大其辞呢?
宋乃娴: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是吃饱了的人也叫,饿着的人也在叫。我认为目前过渡时期在具体问题上不要一刀切。比如说有的项目,开发商已经开始干了,已经都投入了一部分钱,银行一下子提高了门槛,他的资金链就要断。断了对谁都不好,对开发商不好,对银行也不好。项目变成了一个烂尾楼,开发商也不可能还银行的钱了。所以已经有投入的、好的项目银行应该继续支持。
如果房地产都停下来的话,对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水泥、钢材、能源等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大家都在胡嚷嚷。有的人可能刚好拿到地,还没投入,这时再观望一阵,可能对他还有好处,因为土地控制住了,金融控制住了。对于把商品流通作为主业又搞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因为有流动资金和短期贷款影响不大,而以房地产开发作为主业的企业,产品单一,没有别的资金渠道,银行贷款的门槛提高后就可能出问题。所以,银行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具体分析的话,半拉子的项目、半拉子的工程都停在那,它就不可能再创造价值。没有价值,它就还不了你的钱,它死你也死,你又造成新的不良资产。
过去我们的金融没放开,都吊死在银行一棵树上。现在银行门槛提高了,也就逼着开发商到市场去寻找新的出路。对于外资来讲,现在正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好时机。比如说基金,现在国内搞基金还不成熟,有的就到国外去,和国外的有些基金搞共同发起人,成立基金后再把资金投入到中国。另外,把项目作为平台,和国外的投资机构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来寻找新的出路。像摩根士丹利和金地置业,洛克菲勒、美林、汉斯,都已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中国,这也是个好事。咱们很多事情往往需要一种市场的推动,也需要开发商的推动,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救市”也不是大家在耸人听闻,我听说5月份我们的销售额才是3成4成,这确实就有问题了,往下干起来就难了。所以,对于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项目,银行该贷款还得贷款。国家可以对高档别墅的贷款有制度引导,对搞投机的要有所控制,这些都是必要的。国家现在阶段性地这样做,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逐渐随着市场的规范,法律的健全,任何市场,不光是房地产,都要用市场的杠杆来调节,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的一刀切造成的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
宋乃娴:北京的房价,能跟西安、兰州比吗?西安、兰州现在的房地产开发才刚刚起步,北京、上海已经是非常发达了。上海进去了一些热钱,它的房价有泡沫的成分,那就要给它吃药。要给西安、兰州也去吃药,它只能死。上海和北京都不一样,北京的情况就比上海好得多。最近我沿着八通线到通州一带,看到有2000-4000元一平米的房子,老百姓买得起,所以北京就比较平稳。
姚敏:就是说北京的房价总的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宋乃娴:它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年轻人,结婚需要房子,市中心的买不起,可以到外边去买,照样能解决安居乐业的问题,而且交通非常方便,坐地铁一个小时就到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产品解决大家不同的问题。如果一味地为了挣钱,都去建高档住宅和别墅,没办法解决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那老百姓肯定就要闹,社会就不安定,就不符合国家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北京的市场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大量的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因此它的房价的基准就比较合理。上海、南京几年前就没经济适用房了,所以它的价格就显得特别高。其实北京高档别墅的价格也不低,像贡院6号一平米就得几万。但是由于北京市场已经分出各取所需的层次了,因此就不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社会的和谐。
姚敏:结构比较合理?
宋乃娴:相对来说,结构就比较合理。国外也是这样,伦敦、纽约最好的地方也是国外的财团来买,你不能说它是不合理的需求,它体现了伦敦市中心的价值就是高,你有钱你来买,我在交易税各方面都收得非常高,政府收到钱后用来搞公共事业,这样才能解决低收入的人“居者有其屋”的问题。我们将来的发展必然也是这样。北京上海的中心地带,就是寸土寸金的地带,是谁有钱谁来买,世界各地都可以,但是不影响我本市居民“居者有其屋”的问题,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房地产的发展方向。
德国就是这样做的。开发商在这儿盖一栋楼,这栋楼里他必须拿出40%按成本价卖给中低收入的家庭,多出部分政府从财政上付给开发商。包括北欧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政府在行政上的宏观调控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通过市场的杠杆来平衡社会。企业的发展靠市场的需求;政府的责任是为企业和市民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税收是政府的钱袋子,是创造良好环境的物质基础。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和谐。
房地产市场的培育有一个过程
姚敏:现在有的开发商也提出来,作为商人他们肯定是逐利的,因此,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应当由政府出资解决,对此,您如何看呢?
宋乃娴: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实际上就是由政府出资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但是要全部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还不现实,主要是国家的财力不允许,要有一个过程。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20多年,中国真正的住房商品化是从1992年开始,土地的商品化也是从1986年成立国土局开始的,所以说发展的时间还非常短,很多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房地产业中的各方利益无法通过法律、法规确定下来。既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影响到金融、房地产的正常秩序。所以要有破有立,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培育,使政府有能力、有精力解决中低收入住房问题。
谈到房地产暴利问题,应该说与房价关系不大。因为过去房地产利润高主要指的资金的利润高,而不是房地产项目利润高。项目利润(除个别高档项目外)就是大约18%-20%,属合理范围。而资金利润,由于过去银行贷款门槛低,土地不需要挂牌,因此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自有资金1-2亿元就可启动,后续资金可以找银行。若项目利润按20%,利润为2亿元,相对1-2亿元自有资金的投入,利润就很可观了。现在银行的门槛抬高了,土地的取得要挂牌了,自有资金投入大了,暴利就难了。
姚敏: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来说,也会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
宋乃娴:是重新洗牌。那些没有资金的小公司肯定就不行了。长江实业当年的东方新天地,建设、出租经历了10年人家都不怕,为什么?人家还有其他的资金可以来回地运转。所以我们将来就会出现一批非常有实力的开发公司。没实力的,要不然就倒了,要不然就跟别人合作了,我觉得这对规范房地产市场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姚敏:房地产业是政府收入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现在一些地方通过大量地卖地来积累城市的建设资金,因此对于中央政策的实施,可能就会由于所处的地位和立场的不同而有所保留,您对此如何看呢?
宋乃娴: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也还是时间问题。1986年成立国家土地局,才有了国家土地的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到现在来说应该还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土地从过去的无偿划拨变成现在土地是商品,是有价值的了,而这个价值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配;这个价值国家(所有权)和个人、企业(使用权)如何分配;这个价值是一次性体现还是长期体现,都直接影响到土地的使用。这届政府为了政绩和利益就把土地卖掉了,可是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你卖掉了,将来再上来政府怎么办?所以现在说的征收物业税什么的,就是不要一次性把钱都花完,而是要陆续地、要长远地来做这个事情。
土地作为商品,它的价值我们应该如何体现出来?现在应该说还不完整,不合理。土地应该要反映它长期的效应,既然它是不可转移的,不可再生的,它的价值就应该长时期地作为国家的资产来使用,现在说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属于个人和集体,但是你把这地完全卖给了土地的使用者(也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还怎么体现出来呢?体现不出来了。所以对于作为商品的土地的,它的表现形式我觉得现在是不合理的,因此就造成了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利益的驱动。现在就是这届政府能卖多少卖多少,拿这钱搞广场搞道路,完全不管以后的怎么办。土地的价值要细水长流,才能使不单这一代人得到好处,要子子孙孙在土地上都得到好处,你才反映出土地所有者的价值。一届政府5年,因此就造成了短期行为,这届政府卖的越多越好,以后再想发展生产,再想搞大的项目,没地了。所以说,法律和法规非常重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完善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完全看GDP
姚敏: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业发展得比较快,这个城市的GDP就比较高,现在我们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会不会影响城市的总体经济水平呢?
宋乃娴:我认为,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完全看GDP。我们现在的城市,越是发达的城市,老祖宗留的东西越少。倒是泸沽湖、丽江留存的文化价值更多。就是交通不发达,它在那个地方放了几年,结果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好。所以,一个城市不是说它的GDP上去了,这个城市就是最发达的,我觉得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国家对它的要求也应该是不同的价值表现。有些城市就不应该通过房地产来增加它的GDP,而是通过旅游,通过它的自然资源,通过它的历史资源来使它的城市发展起来,最终使它GDP提高,而不是速成。当然了,现在修10条马路,GDP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要考虑现在有没有必要修10条马路,这个城市根据目前的交通量,目前的人口需求,可能搞5条就行了,而不能为了追求形象工程,或者为了追求GDP,来这样做。而且当你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精髓都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就这样做,肯定会失误。现在城市的千城一面,就是单纯地追求GDP,单纯地追求所谓的城市现代化造成的。我们现在的城市就是闭着眼睛一睁开,不知道是到了哪个城市,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最忌讳的,为了追求现代化,失掉了城市的个性,作为城市的领导者,要了解所在城市的自然资源、历史的渊源、已经积累的财富,才能建设出有个性的城市,这个城市才是有生命力的,所以不能单纯地追求GDP。
姚敏:GDP只是一个指标?
宋乃娴:对,只是一个指标。不同的城市应该通过不同的形式,最后达到GDP的提高。实际上最后要达到的是什么呢?达到这个城市老百姓的富足和老百姓生活的其乐融融,而不能够光追求数字。数字再高,你的老百姓生活不幸福,老百姓过得不安逸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对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要求,通过不同的手段和层次,利用它自己的资源,来发展这个城市的经济,最后达到GDP的提高,最终达到这个城市的真正的繁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小城镇
姚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和城镇人口进入城市,对于他们的住房需求,应该怎么解决呢?有人提出建廉租房的形式,您对此如何看呢?
宋乃娴:廉租房实际上政府一直都有,也在这么做着。很多城市都是这样,一部分房产局的手里都有廉租房,而且这确实是政府要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的一条途径。现在对于城市化的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城市化的问题,不是使大城市无限地扩大,更重要地是要发展小城镇,这有利于解决城乡差别,解决人口的贫富差别,解决农民和城市人收入的差距。而不是把大城市的人口无限地增加,建设得特别好,我觉得不应该走这条路。
姚敏:不应该大家都挤到大城市来,要提倡就近解决的原则?
宋乃娴:过去我们规划经常讲“城市病”,确实这在大城市是存在的。不要到国外去,在国内你也可以看到。有些小的城市生活非常舒适,大城市的生活就不舒适,它的污染问题、水资源问题,城市的卫生问题,食品的问题等等都会出现的。我们要城市化,但是城市化要有大城市,也要有农村周围的一些城镇来吸纳农民工的进城,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小城镇离家更近,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出来打工,农忙的时候又就近回去种他的庄稼,这样还解决了我们交通拥挤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农村周围发展一些城镇,就比搞几个大城市要好得多。从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搞廉租房是一条道路,而且我们很多城市也在这样做。
姚敏:具体到北京的情况如何呢?
宋乃娴:北京在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前几天听广播,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筹集资金建设廉租房。我相信全国所有的城市都会重视这个问题。
姚敏:也会加大这一方面的力度?
宋乃娴:也会加大这一方面的力度。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之下的人,有人会得病,也会有残疾人,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政府就有责任来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姚敏: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网友评论
暂无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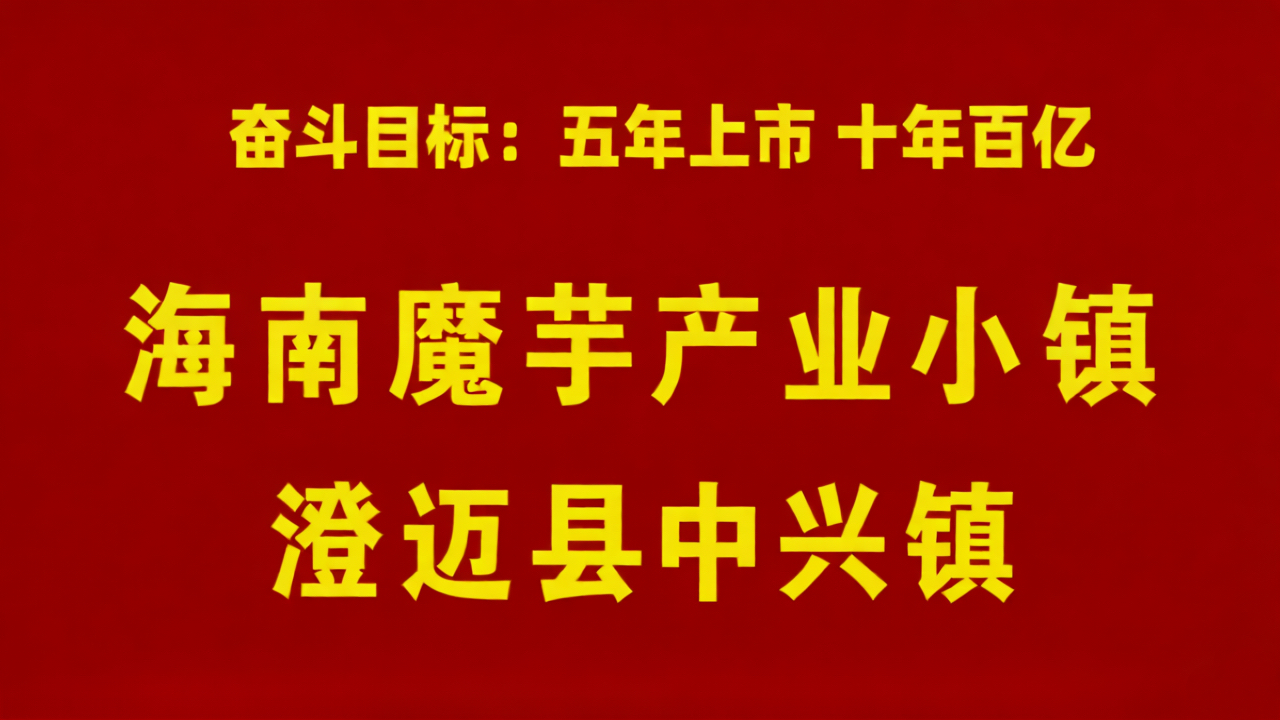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